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姜振宇
我们正身处“未来”,一个全新的“科幻时代”。
21世纪是那些曾身处现代化浪潮中的人们反复想象、期待并描摹的时代。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人类并未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科幻小说家们通常保持一定的警觉性,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投入于创造那些更为悲观、因而也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
实际上,科幻作为虚构文类的根基正在动摇。科幻的魅力总是有赖于作者和读者对科幻这个文类的某种“共谋”:你知道这是假的,我也知道你知道这是假的,但我就是为这种幻想着迷。然而,现在这种假的要变成真的了。
科幻作家们当然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挫败。上世纪中叶的阿西莫夫们和克拉克们总在讨论登陆月球,但他们从未想到会在电视机荧幕上直接看到登月直播;这个世纪的陈楸帆和刘宇昆们创作了无数机器人故事,但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表演的手绢舞显然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更不用说每个移动终端都普遍应用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突破人类想象极限的纳米级芯片,这些情景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得司空见惯。正如韩松所说:“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得过它呢?”
科幻的历史伴随着科技发展,呈现出一种如钟摆般的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科幻转向羸弱不堪、深陷“政治正确”、聚焦鸡毛蒜皮之日常以前,七八十年代曾涌现出第二波太空歌剧与赛博朋克的热潮——前者渴望重返星空,后者则强化技术对身体的入侵。这二者本质上是对兴盛于六十年代的“新浪潮”科幻的纠偏。新浪潮沉迷于幻觉、意识等“内部空间”的探索,其偏重之处在于对二战至冷战时期“黄金年代”科幻所标榜的理性与宏大野心的反叛。若再往前追溯,“黄金年代”之前的世纪之交,更有混乱、非理性的“克苏鲁”神话源起,和威尔斯将科幻作为讽刺利刃;更早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则充斥着美国粗犷初生的“太空歌剧”(也许直译成“太空戏”更合适)和欧洲凡尔纳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科技的热烈拥抱。
从科幻的发展历程可以见得,在求学时代就目睹了科技侵入生活的作者们,似乎总是失去构造技术奇观的勇气;感受过科技雏形之粗陋的作者,反而更擅长从正面去描绘未来的宏伟。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显然都身处前一种情境之中,并且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颠覆的时代周期之中。
中国科幻该怎么办
中国科幻并不是自今日才开始面临危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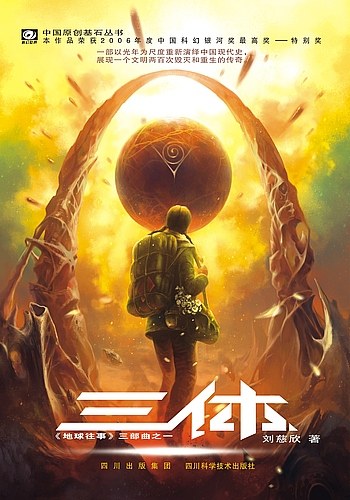
2006年9月,正当《三体》因被出版社拒绝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而不得不在杂志上连载的时候,科幻作家韩松和科幻作家兼学者吴岩进行过一次对谈,主题为“科幻文学期待新的突破”,但它探讨的是“当前中国科幻文学的衰退,以及它是否会走向消亡?”
韩松、吴岩的观点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悲观倾向。当时,虽然诸多革命性的科技已经见诸新闻报道,但它们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还相去甚远;创作方面虽有一些亮点,也基本局限于小圈子内。因此,一方面呼唤以创新手法释放科幻美学的潜力,另一方面则认为这一文类的范式正趋于穷尽,其功能将被其他文学和文化形式所取代。
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当初的判断,而且其中许多预期都以更加乐观的方式得以实现。在文类之内,刘慈欣等作家不仅复兴了上一个“黄金年代”科幻朴实刚健的气质,还深深根植于中国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和作者本人的个体记忆。一种与欧洲式精英科幻及美国式通俗科幻相区别的全新的中国式科幻正在逐渐成形;在文类之外,科幻的审美内核也在“圈外”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接受度。电影、动画、漫画、游戏、小说不再畏惧“科幻”的标签,产业体系已将“科幻”纳入分类统计的框架之中。
然而,这种乐观的现实更像是在资本市场驱动下催生的一种假象,难以掩盖因“我们无法理解和把握被科技所改变的现实”而产生的集体焦虑。正如科幻历史中规律性出现的科幻风格的左右摇摆,科幻的使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诚然,科幻依旧如吴岩所言,是“科技与未来对现实的双重入侵”,但重点已不再是奇观性的部分,而是“入侵”。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缺乏的不只是对科技的理解及对未来的幻想,更是对正在变化的现实进行描述的语言——科幻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描述现实,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功能。这甚至比对科技和未来的想象更为紧迫,因而在当下也显得更为重要。
好在这不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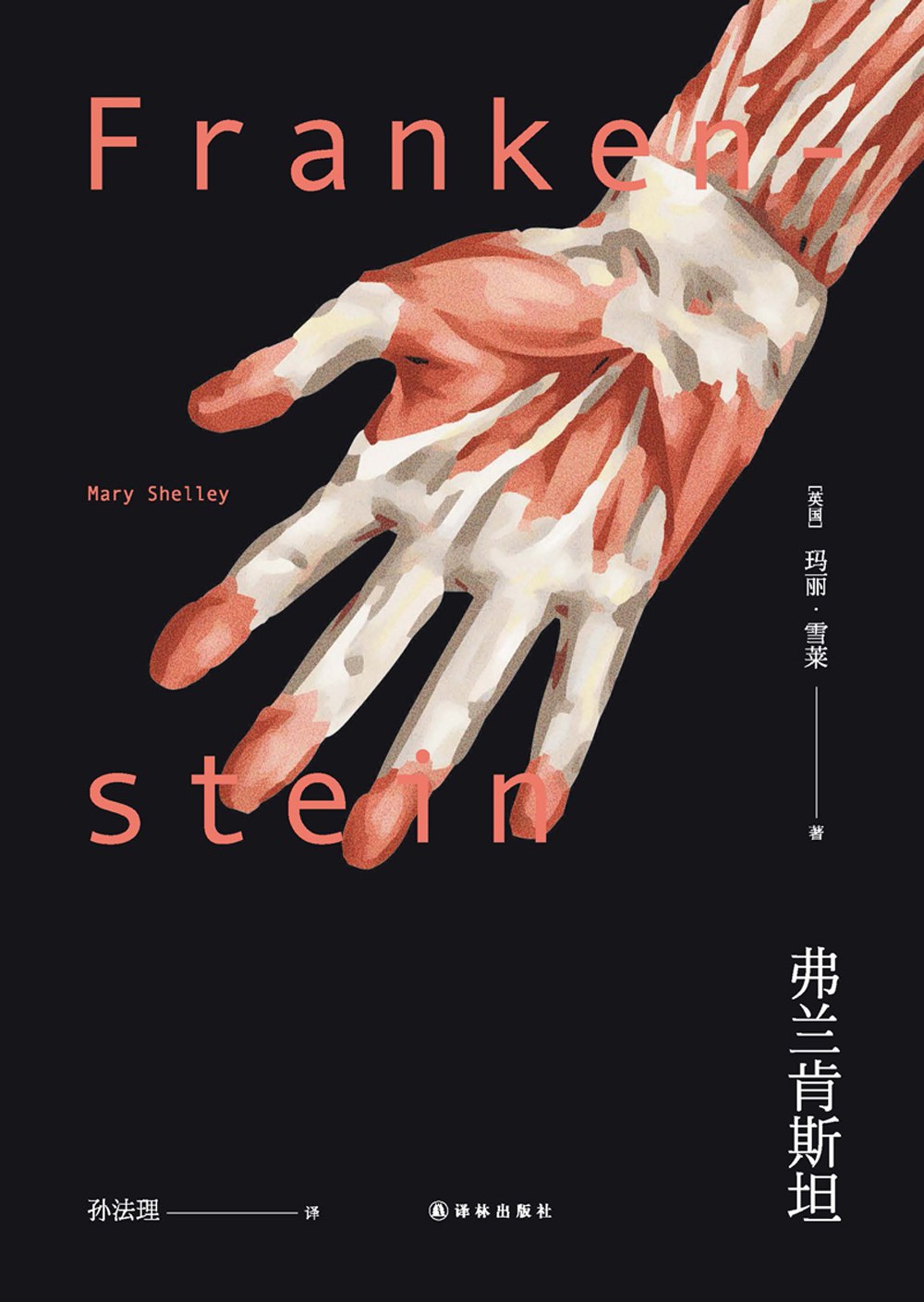
当雪莱哀叹于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诗人们的接受能力时,玛丽·雪莱创作出了《弗兰肯斯坦》,将科技意象深深嵌入人类情感之中;当卡尔·萨根惊讶于火星故事中出现的荒诞错误时,他主导拍摄的《暗淡蓝点》为后世几代人留下了受益不尽的宇宙级审美体验;当刘慈欣感慨于中国80年代的科幻沦为“消失的溪流”时,他从科幻迷变为了科幻作家。当“主动介入”科技洪流成为当今人类必须做出的选择时,科幻也已不再遥远,变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每个人都面临着科技带来的困惑,以及需要深入理解的现实。
“科幻”助力人类描述时代
“科幻时代”理解现实的核心特征在于:它并不对好与坏进行定义,而是关注于人在情感、文化、观念、方法等范畴中不得不做出的变化,并认可这种变化的合理性乃至正义性。至于随之而来的不安、焦虑、困惑乃至不公,则类似于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而不得不承受的难产风险、腰椎和颈椎疾病、踝关节等问题,这些都是必然的变化,并且遵循着可把握的规律——只是目前我们仍将其视为伤害,而非特征。
在当今的科技实践当中,科技入侵生活的规律固然可把握,可仍需要作家调动自身的经验、智慧,以及生花的妙笔予以具象化。《流浪地球》《三体》中微妙的代际传承,根植于刘慈欣亲历的大型国企中的人际生态;《中国轨道号》对集体事业的礼赞,源自吴岩在军属大院与科研院所内的童年回忆;《小镇奇谈》承载的是七月身为“三线建设”后代的切身经历;《大冲运》则直接脱胎于马伯庸所目见的春运图景。科幻作家们的独特魅力在于,他们不仅相信人类现代化历程中所出现的繁复“现象”背后存在着规律,更能洞察到“发现规律”,即理解现实这一过程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意趣。
我们的困惑来自未知,或者虽然知晓,却无法言说。在这个“剧烈颠覆的时代周期”,我们依旧有足够多的迷茫和惶惑,当然需要科幻参与纾解。我们如今思考的“人形机器人”“元宇宙”“人工智能”,都曾是可能性被科幻几乎穷尽的话题,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意象和词语来统一描述。而我们一旦全然知晓,科幻的惊奇感便会迅速褪去。我们已经不记得鲁迅在用圆规呈现“细脚伶仃”之时,为什么要预先说明圆规乃是“画图仪器”中的一种;我们也很难觉察到凡尔纳笔下的潜水艇和神秘岛,有什么直指人心的神奇之处——他们已经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审美的记忆当中了。
或许对科幻来说,仍有困惑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