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马晓光
“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是近年来文学界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这是一个形成时间不长,并且仍在不断变化扩张的群体概念,大致指以双雪涛、郑执、班宇、贾行家等“八零后”作家为代表的一个群体,兼具年龄、地域、独特的创作风格等多重标签。通常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是以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获》杂志上的发表为标志的。随后的几年中,《刺杀小说家》《仙症》等多部小说经影视化改编获得了广泛关注,因而他们的作品进入大众传媒的视界。

白山黑水与钢铁荣光:“新东北作家群”的渊源与传承
在这批年轻作家涌现之前,东北籍作家在当代文坛早已屡领风骚,如文坛出现了以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以及凭借长篇纪实文学《巨流河》蜚声海内外的齐邦媛等。
再往前追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东北作家群”于山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崛起,用自己的热血开启了抗日文学的先声。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体悟,与东北大地广袤的黑土、无尽的莽林和铁蹄下不屈不挠的人民融为一体,铸成血肉,凝结出一种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粗犷沉郁的地域特质。其作品中挣扎奋起的生命张力,时至今日读来都颇具令人感奋的力量,一如萧军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中质朴刚健的反抗精神,亦如萧红作品中带着独特女性视角的哀伤与撕裂。
相近地域的作家之所以能形成并称之为“群”,在于他们具备了观照视野与母题呈现上的共性。如果说八十多年前的“东北作家群”主要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集中回应的主题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二者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然而细究不难发现,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热衷于展现地域性特征下具有全局普遍性的时代创伤,尤其是那些留在每一个小人物身上的深刻而鲜明的命运烙印。正如黄平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中所述:“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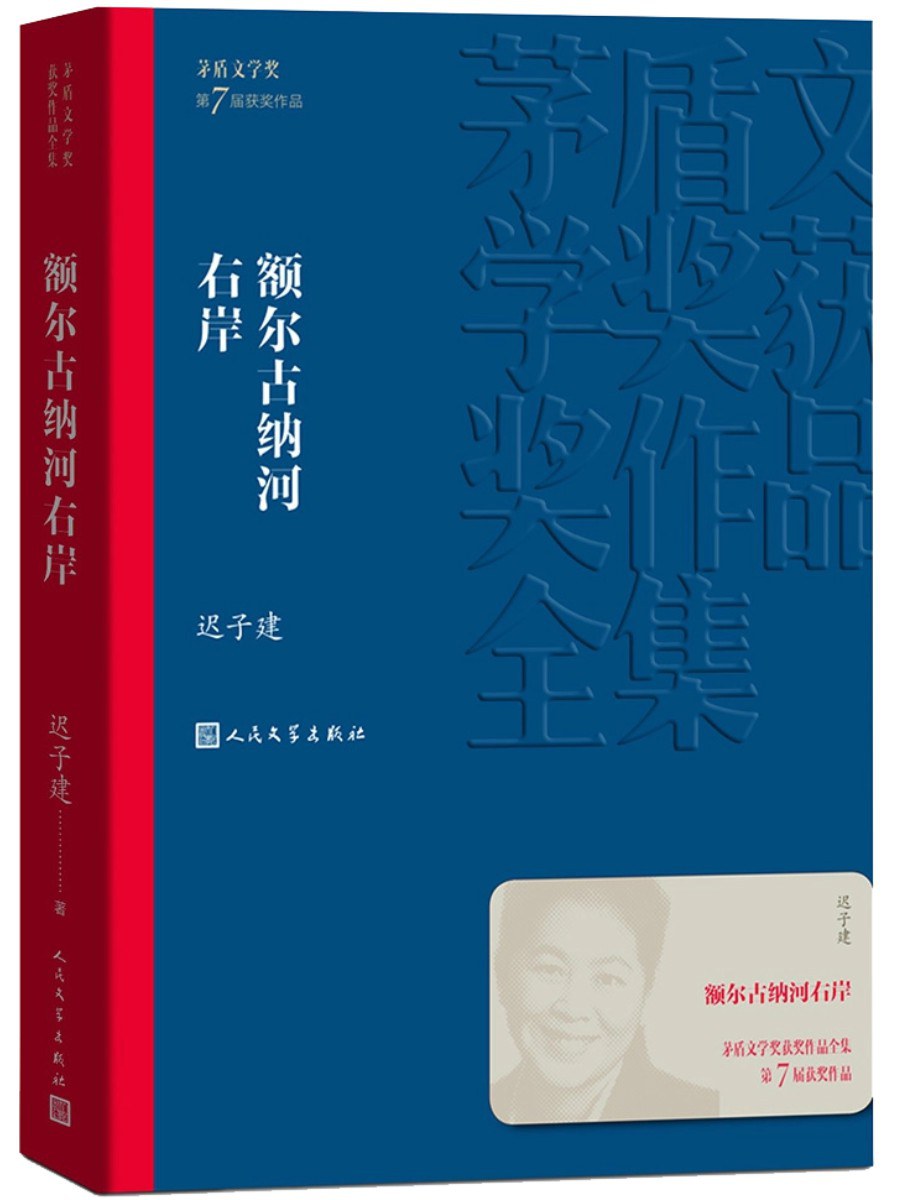
挥之不去的破碎感:“新东北作家群”在时空两维上的呈现
文艺作品向来偏爱盛极而衰、繁华凋零的气质,“破碎”可以说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普遍沉浸的一个母题。东北文学也有过“闯关东”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围绕社会学意义上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历程展开,自带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质朴的浪漫主义气质。然而能够带来更长久传播力和更广泛的情感共鸣的,还是上文所述的抗战和下岗潮两个破碎又幻灭的宏大主题。前者展现了深厚的农耕自然文明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国困境和生存之境,后者则是已然发展到高峰的工业文明与后现代语境发生碰撞时的崩溃、挣扎与彷徨。
在叙事策略上,“新东北作家群”常采用父子两代人的双线结构,以伦理问题隐喻时代创伤。改编自短篇小说《仙症》的电影《刺猬》于今年八月在大银幕上映,抒写了一出关于两代人理想的破碎与重生的家庭喜剧(抑或是悲剧)。王战团和周正虽是姨父和外甥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生命传承和精神延续。相比之下,周正与亲生父亲的关系则充满压抑和反抗,撕裂和对立,直到最终也没能完全和解。神话叙事中既存的父子对立母题,在这里结合着“下岗潮”后东北的衰落萧条、固有权威丧失后的迷茫、父辈往日荣光的消散等时代背景,从而营造出一股挥之不去的破碎感。其与当下大众传媒领域火热的“东北风情”地域审美存在某种带着间离感的吻合,同时亦表达出更具普适性的理想主义幻灭与重生的时代之惑。
现实主义写作的赛博重构:“新东北作家群”之新
“新东北作家群”之“新”,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得以考量。
其一,是出场方式的新。一般认为,他们甫一出场,即超出单一的纯文学场域,而是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打通了纯文学与市场受众的边界。他们屡屡斩获各大新旧文学奖项的同时,也赢得了广泛的话题性和关注度,从而天生具备了IP属性。
其二,是新的叙事策略。普遍来说,“新东北作家群”在创作风格上重视情节矛盾的推进,追求故事的悬疑感和传奇性,叙述多依赖对话与细节的描写而较少展现心理活动。从中不难看出“80后”作者群体对于影像化呈现的文本敏感性。如已经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平原上的摩西》,小说不单涉及家庭成员间的爱恨情仇,还以颇具悬念的拼贴式手法,在叙事拼图中融入严打、下岗潮等时代性事件,揭示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人性的复杂。这套策略高度符合近年来具备一定市场效益的类型化“文艺片”的运营惯例。
其三,是新的生存空间。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东北宇宙”不算“新东北作家群”的独创。赵本山从央视春晚掀起了一股东北小品热,随后又在《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故事》等故事中衍生出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东北农村形象。再如《钢的琴》《白日焰火》等影片在国内外获奖频频,将一个“铁锈味”浓厚的灰暗东北定格在影像中。也不乏开心麻花团队的《夏洛特烦恼》、大鹏的《缝纫机乐队》等充斥着昂扬乐观精神的“东北工业喜剧”影片。这些风格、题材各异的作品,不仅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层面的东北影像世界,更形成了一种只在网络语境中存在的“东北赛博空间”。受众关注的往往并非真实的东北,而是在这一介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群体狂欢。“新东北作家群”作品影像化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融入且顺应了这股媒介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票房超10亿的双雪涛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刺杀小说家》,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现实与小说交织的奇幻世界,探讨了信念与现实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这部作品已然完全跳出了“东北”这一时空藩篱,以更加多元的叙事方式打造出一个架空的赛博空间。然而剥开光怪陆离的视听元素,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故事的内核依旧是那个后工业时代父辈的凋零落幕与子辈的迷茫叛逆并存的东北大地,而在故事的更深处孕育着重新挣扎奋起的信念,那种曾在白山黑水间开天辟地,在钢铁洪流中滚滚向前的力与美。
正如阿里影业开发总监霍耀武所说,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改编价值,常常要通过如下几个层面的考量:文本是否有突出独特的类型或题材,人物是否有传奇性和内在生命力,情感表达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从中看到历史的回响、对当下的观照等。可以说,“新东北作家群”除了具备在文体实践方面的先锋性之外,还体现出了高度的传播自觉性以及与赛博时代的紧密相拥。“破碎”是一种对生存境遇的反思,亦是一种个性化策略,其目的不是“破碎”,而是为了在另一层面获得重构与再生。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讲师)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