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江飞
毫无疑问,《破壁与神游》是诗人陈先发截至目前“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是涵括其生命与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编年史的体例,精挑细选各个时段最具代表性的短诗、长诗、随笔、访谈等作品近200首(篇),编为五卷,煌煌600余页,第一次全面集中地展现了陈先发生命之流的历程和诗学之思的进程。在困境中破壁,在语言中神游,诗人苦心经营诗文近四十载,终成就其以“生命”为内核的丰盈高蹈、独树一帜的精神面相和生命诗学(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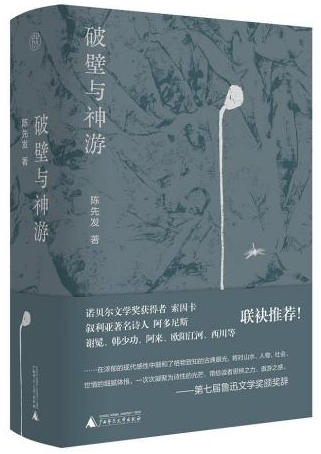
何谓诗?诗又何为?这是摆在一切诗人面前的灵魂之问。在陈先发看来,“诗的力量来源,最本质的东西是诗所蕴含的生命意志,而不是修辞本身”。换句话说,那些堕入修辞牢笼和语言炫技的诗,不过是些没有人气、没有生命力的“死诗”罢了。“诗是原初的、浑然的生命力,语言是具象的生命体,而词是这个生命体上的器官、肢体、动作”。以“生命”赋意“诗”“语言”和“词”,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观的承继,也是对中西生命艺术观的会通,更是诗人从自我生命出发的体认。“人,其实只是自身的一个瞬间,短暂肉身的寄生时段。个人史中所遭遇的一切,必然地要化作语言资源”。正因如此,父亲死亡的瞬间成为其个人生命史中一而再、再而三闪现的痛点,化作“写碑之心”;而在黑池坝散步神游的时光,则化作几百万言百无禁忌的“黑池坝笔记”。
正如人的“生命”不是身体器官的简单拼接,诗歌的生命力在于“气”的灌注充盈,在于“充实之为美”,在于“气韵生动”,乃至不可被解构的神性。这种生命力形之于言,就呈现为词与词、词与物、物与物的各种关联的力的和谐关系,生成一种与诗人生命相互映照、彼此成就的语言生命体。而这种作为语言生命体、具有生命力的诗,自然也对读者阅读提出生命的召唤,“你得进入它的语言氛围,去随它一起呼吸,感受它长在具体事物细部上的血和肉,触碰它的体温”。比如颇负盛名的《前世》,“他们纵身一跃/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重构“梁祝化蝶”的古典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灵真相和生存实境;比如《丹青见》,“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重建自然秩序,揭示沉默的世界高于喧哗的世界、死高于生的意义。归根结底,诗人意在书写生命力之美,赞颂人的情感与生命意志。及至最近的组诗《了忽焉——题曹操宗族墓的八块砖》,“壬寅年春末。我是烧制墓室砖块的窑工/手持泡桐枯枝在/未干的砖坯写下/断断续续的字句/给了这黏土以汗腺与喘息”,诗人化身千年前的窑工,神与物(文字砖)游,表现了一种突破时间和空间之有限性的生命力,一种带有历史体温又洞穿历史的生命意志。无论读短诗还是读长诗,读者都必须进入诗人用“四重现实”——感觉的现实、再选择的现实、现实之中的“超现实”以及语言本身的现实——所营构的氛围和气息中,都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体贴诗的生命,设身处地,以心会心,这是诗人对困于四壁、囚于物役的现代读者的良苦用心。
对于诗人而言,在面壁与破壁之间,需要虔诚而持久的耐心,尤其需要建立与生命自觉相应和的文学自觉,需要在自我和他者、个人与时代两个向度上进行生命开掘。“对人的命运,予以最深沉的凝视,完成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洞见,而且这种洞察能够超越时间局限,这才是最为动人的诗。”这里的“人”既是指自我,更是指他者。对自我的开掘就是发掘个体生命的困境,寻找真我,就像周伯通那样“左右互搏”,就像佩索阿那样“让一个人裂变成一个群体”,“让一己生命的无穷丰富和矛盾彷徨毕露无遗”。而对他者的开掘,就是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去关怀他人生命、思考时代生活、认知历史真相,就是摆脱“影响的焦虑”,从因袭模仿的“无我”之境走向诗歌自觉的“有我”之境。
这种“有我”是“以我观物”,是对自我与他者之关系、个人困境与时代困境之关系的洞察与揭示,本质上是一种“觉他意识”。“握着我的树枝到诗歌里去/为它一哭,我前后彷徨”(《树枝不会折断》),“我仿佛耗完了自己坚硬又幽暗的内心”(《与清风书》),如果说早期的这些诗作还耽于“小我”之情思的话,那么,到《姚鼐》《白头与过往》《你好,街道》《口腔医院》《写碑之心》《枯七首》《风七首》等长诗与组诗,则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调和气息,不再是书斋里的低语,而变化为旷野上的风暴。这“风暴”的中心,不再是个人的困境,而是人类的困境、历史的困境以及时代的困境。
当下,科技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可谓时代困境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对此陈先发早在2020年便倡导了一场以“科创之光”为名的天鹅湖诗会,探寻“量子时代的诗性表达”,因为在他看来“最具有生命力的新生长点必在其中”。在DeepSeek等人工智能不断震惊世人的当下,这显然是对人类生命力和诗歌生命力的双重期待,是乐观的而非悲观的,是开放的而非保守的。
“破壁”意味着完成一种思想的涅槃新生,“神游”意味着开启一种精神的自由解放,正如“枯”的困境孕育着“荣”的可能,有限必然追求无限的永恒。如其所言,“艺术说到底,是个体生命力的激发,是一个易朽与短暂的生命体,在孤独时告诉自己如何去追逐那不朽的愿望”。陈先发数十年如一日,凝神专注于自我与他者生命力的开掘和诗歌生命力的重建,潜心浸淫于语言生命体的本体创造,这是一种强悍的个体生命意志的显现,也是时代对存在真理之守护者的生命诗学(美学)的馈赠。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