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张慧瑜 钱嘉欣
《惹作》中那段关于大凉山女子苦惹作喝下百草枯的描写映入眼帘时,许多读者都会被文字营造的沉重氛围所震撼——“她慢慢走过一片剩残株的苞谷地,走过一条积雪的泥泞土路……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牛粪的味道、煮洋芋的味道,以及宰杀牲畜的血腥味的死亡气息”。这段细腻的场景描写也引发了读者的讨论:在非虚构写作中,这样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学化表达是否越界?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我们该如何把握真实与想象的边界?这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国非虚构写作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深层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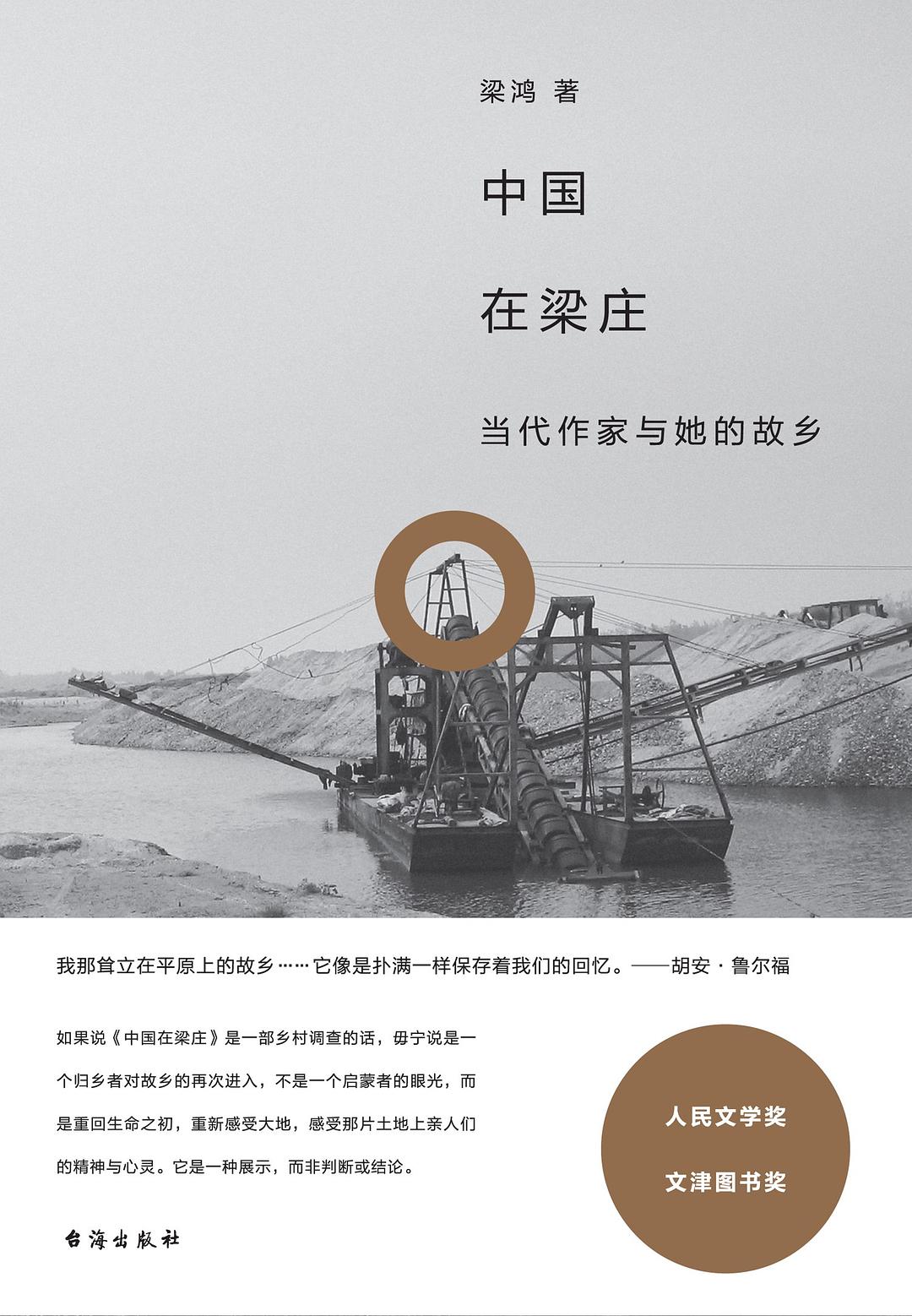
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
回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条其从“记录工具”到“文学创作”的演变轨迹。上世纪30年代,作家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作家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开创了报告文学的先河,那时的作品更像是时代的快照,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现实使命。随后,纪实性题材承担起塑造典型、服务生产的社会功能。到了80年代,报告文学再度兴起,多聚焦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并与突破“禁区”的新闻报道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载体。2010年以来,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被引进,出现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样的佳作,通过对乡村变迁的田野调查,展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读者需求的多元化,一批文学意识显著的非虚构作品开始涌现。从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到易小荷的《盐镇》,这些作品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主动暴露叙述人,尝试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及细腻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读者与笔下人物产生深度共情。这种转变让非虚构文学摆脱了“粗糙”的标签,却也带来了非虚构写作是否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争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非虚构写作天然存在的矛盾性——它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要求的“真实”在于书写的对象应当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对于人物、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则与书写者自身的调查、理解和阐释有关,所有叙事都需经过叙述主体的筛选、重组和语言转化。因此,非虚构书写经常呈现出两种风格,一种是追求客观化、白描式的写作,尽量搁置书写者的个人因素,展示书写对象的某种原生态和“真实”状态;第二种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内心体验的观察,往往讲述自己深有感触的经历。这就涉及到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同时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张力和优势所在。
此外,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非虚构写作的特点恰恰在于暴露第一人称叙事的现场感。这种不假装客观的叙事角度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也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叙事者对于真相的阐释。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并非彼此平等——书写者是具有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主体,被书写者则是客体化的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博弈。这种博弈和阐释的边界缺乏严格的标准,但非虚构写作期待和呼唤着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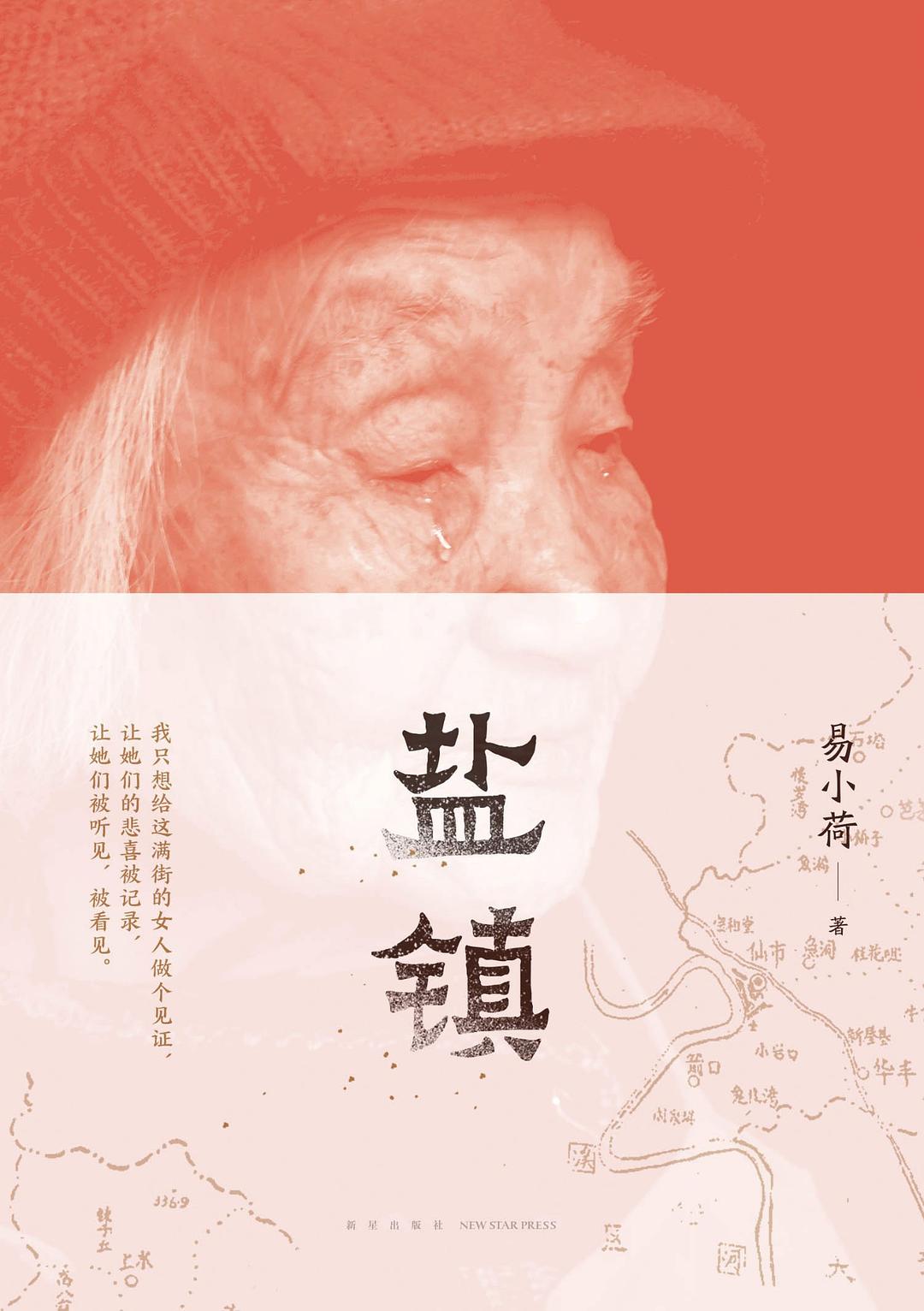
非虚构文学《盐镇》
更复杂的是,非虚构写作还承载着特殊的社会期待。在这个虚拟世界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真相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非虚构作品通过一个个“事实”“亲历事件”,将边缘群体的生活呈现在公众面前。读者期待从这些作品中看到未被遮蔽的现实,获得认识世界的新维度。当《梁庄十年》展现乡村变迁时,当《盐镇》聚焦女性生存状态时,它们都在履行这样的社会功能。但当文学技巧的运用让读者开始产生对真实性的质疑时,非虚构作品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这种信任危机正是引发争议的深层心理动因。实际上,当下的伦理争议并非坏事,它提醒我们非虚构写作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更有其作为一种“元写作”的价值性。当我们讨论非虚构作品的写作手法时,其实是在共同探索非虚构文学的中国路径。
那么,非虚构写作中的“虚构”边界该如何界定?它需要以真实事件为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借助虚构和想象力进行加工。这种想象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事实核查之上,不能凭空捏造核心情节、人物情感或受访者观点。而对于非虚构写作中的“文学性”,我们应当对其持有更为包容的态度。因为任何叙事都是一种阐释,非虚构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实录和素描,而是对事件的解释和分析,它尝试塑造一种真实感,而非真实本身。不同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良性的公共舆论需要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解释和争论。因此,非虚构写作应当被允许拥有个人化的文学性,非虚构写作者就应当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进行文学表达。
非虚构写作既朝向自己的生活、把自我对象化,同时也朝向他人、理解他者的世界和逻辑,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非虚构写作的价值,正在于以这些被转写的真实激发我们对社会的结构性思考,让他者变得可见、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不可感知的经验变得可感知、让历史重回当下。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更像一面多棱镜,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现实的复杂面向,让更多被忽视的群体进入公众视野,让边缘声音被听见,而这种“看见”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当我们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为非虚构写作寻找平衡点时,其实也是在为这个时代寻找更丰富、更立体的表达方式——这或许就是争议背后最珍贵的文学探索。
(作者张慧瑜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钱嘉欣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