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邵 岭
绍兴鲁迅故里景区那面鲁迅抽烟的网红墙引发的争议,随着有关部门表示不会更换墙画以及举报人的道歉而告一段落。但其中牵连到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近日,绍兴鲁迅纪念馆内一面展示鲁迅吸烟形象的网红墙画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图片源于网络)
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应不应该展示鲁迅吸烟”,而是“能否接受人类本身的复杂性”。因此,那些关于“如何看待名人的缺点与不良嗜好”的讨论,不应止步于一面网红墙是维持原状还是推倒重建,而应成为这个时代一场至关重要的理性练习——在信息纷杂、价值多元的当下,生活正越来越成为一道阅读理解题,而非是非判断题。与其寄望于生活在一个所有是非都泾渭分明、所有榜样都洁白无瑕的“无菌环境”里,不如打造一套内在的精神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足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来应对“有害”信息和“错误”观点。
精神免疫系统如何打造?重建“整体性思维”在信息碎片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整体性”,既包括对历史的理解,也包括对人物的认知。
要知道,那些在人类文明星空中闪耀的名字,往往携带着自身的阴影部分,就拿文学与艺术史来说,大师们的瑕疵乃至劣迹从不鲜见。毕加索对待女性的方式令人诟病,海明威的酗酒问题众所周知,波德莱尔沉溺于鸦片,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子女(更不要说私生子)不闻不问,而卡夫卡则与多个女性保持着复杂而痛苦的关系……若以今日的道德标准审视,他们恐怕都难以通过“完美人格”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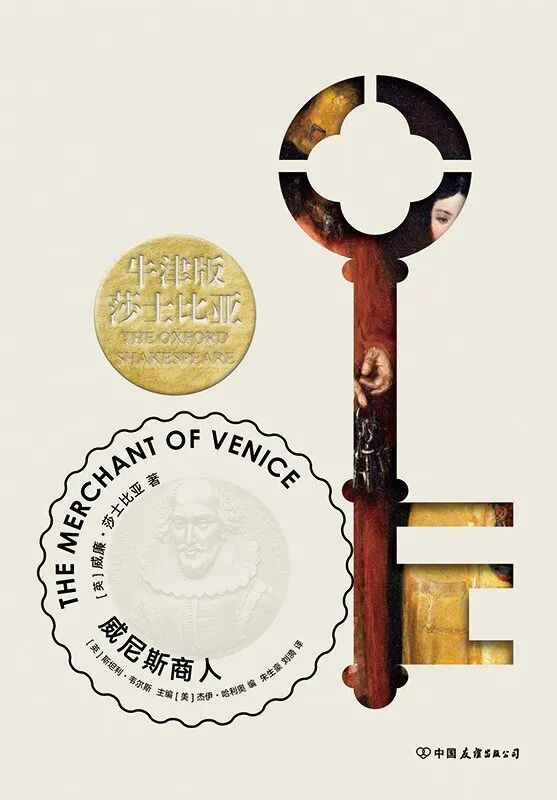
牛津版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图片源于网络)
但正是这些充满矛盾、挣扎与缺陷的灵魂,创造出了人类文艺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瑰宝,为一代又一代提供了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不仅昭示着伟大与瑕疵可以并存,创造力与破坏力可能同源,更提醒我们,将名人简单区分为“圣人”或“罪人”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我们需要的是把人物言行放置于时代与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哪些行为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哪些是个人无法开脱的劣迹。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吸烟在知识分子中是一种普遍行为,甚至被视为一种思考的伴随物;托尔斯泰所处的俄国文化圈,将摆脱家庭伦理视为通向至高境界的必经之路;莎士比亚创作《威尼斯商人》时,英国已通过《犹太人驱逐令》清除了本土犹太社群,欧洲基督教世界普遍将犹太人妖魔化为“贪婪的高利贷者”,这种集体偏见成为其创作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文学与艺术,正是精神免疫系统最好的“训练场”。因为其价值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道德的楷模和模仿的偶像,而在于教会我们如何与不完美的自身、不完美的他人乃至不完美的世界共处。
也许是因为前文所述的大师们自身的经历,许多名作巨著的力量,恰恰源于其对道德模糊地带和人性幽暗面的勇敢探索,犹如描绘出一张人性与世界的认知地图,既有高山峡谷,也有平原沃土。如果只是为了塑造供人亦步亦趋的样板,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应删去伊万深刻的怀疑与反抗,《红楼梦》就该删去贾宝玉的叛逆与软弱。
之所以强调文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现实的复杂性,是因为当前,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存在强烈的“取消文化”倾向,即一旦发现真实或虚构、历史或当代人物的某一行为、观点不符合当下的道德标准,便试图将其全盘否定、从公共记忆中“删除”。
在这一倾向的支配下,被投诉的不只是鲁迅抽烟的网红墙,还有一些童书中的插画和课文中的内容。甚至当爱情题材文艺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不符合“双洁”要求时,也会招来部分受众的不满。而在形形色色的投诉理由里,最常见的一条就是“会对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归因为“绝对正确主义”的泛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恐惧:恐惧失去掌控,更恐惧被伤害,所以宁愿将外部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结构,并要求其在“正确”的框架内运行。
问题在于,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矛盾甚至混乱的。人性亦然。试图打造或期待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环境,是对真实世界的背离。我们需要锻造精神的钢铁,从而在遭遇道德困境、人性矛盾与历史迷雾时,不被轻易地击垮,也不至于陷入非此即彼的愤怒与绝望。正如鲁迅从未许诺一个光洁的乌托邦,却以尖锐的笔触凿破黑暗,让人置身于清醒中,这正是文艺的力量——不回避生命的复杂,而是做一个“真的勇士”,敢于走进混沌、保持思考、依然选择理解与前行。那才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向成熟与文明的精神标志。(邵 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