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编审 叶祝弟
《大河源》是作家阿来2022年探寻黄河源头之旅的一次非虚构写作,是经历了漫长准备、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向中华母亲河之源的致敬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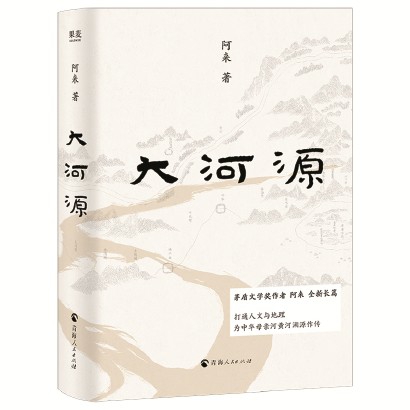
《大河源》阿来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黄河源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边地,又是文明意义上的起点,因此它注定是一个集地理、记忆与文明为一体的复杂存在。河流的历史,本就是一部人与大地互动的文明史,作家与其说是在写边地,不如说是以一个更加宏阔、旷达的视野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变迁、交流与融合、时间与历史等重要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河源》不仅是一个人的地理风景之旅,更是一场朝向文明内部的跋涉,是对中华文明源头的探访之旅。
在《大地和人——一部全球史》中,布利特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和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互动,视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推动力。在这部著作中,地理不是背景,而与文明彼此牵引,共同塑造了世界。无独有偶,在黄河源头,阿来也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了一部关于大地与人的互动史,一部关于民族交流、融合乃至人类共同命运体形成的文明传记。面对人文资料支离破碎的黄河源,阿来找到了写作的关键点:“人与大地,大地与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写此传,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要写,而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书写重点。地理与人文,两相辉映,才是一部真正的黄河源传。”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也是贯穿整个传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整体而言,阿来主要从三个维度切入对黄河源的书写。
第一是地理风物。山峦、河流、天气、植被、动物……在作家的笔下,万物皆有其名、皆有其灵。阿来以一个博物学家的博识与热情,感知并细描了黄河源头那些沉默而热闹的存在,重现了这片土地上的万物“共居”的场景。
第二是历史人文。阿来写地理,满天星斗,但更重要的是写摇曳多姿的人文。阿来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地理考察,“黄河有奇伟的自然传,黄河更有瑰丽多姿的人文传”。作家认为秉持历史学家的严谨介入历史现场,才能打破以往那种空洞的、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的高原叙事偏见。为此,作家借用了包括方志、史书在内的大量的文献材料,甚至神话传说等地方性知识,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文明变迁史。作家并不回避历史上的民族之间复杂的矛盾与张力,自觉站在民族共同体的维度上加以反思和批判。
第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忧思,特别体现在生态的保护与开发中,作家直面生态保护和牧民生产的矛盾,对环境破坏抱以深深的忧思。显然,黄河源不仅是历史的见证地,更是一个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连的现场。在阿来看来,生态保护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修复或者维系,更是在培育新人和再造文明,是一个关乎人类自我认识与文明未来的命题。阿来呼唤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观,一种从人与大地、自然与种群共在关系中生发出的伦理观,或许可以称之为“大地上的伦理”。
黄河远上白云间,如何完成对黄河源的测绘,阿来的选择是行走。对于黄河源这样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的地方,行走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抵达方式,不仅是身体的跋涉,更是一种苦行,一种精神的感知与修炼。在一个资讯发达、各种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行走作为一种方法,具有与“遥知”“远观”不同的特殊存在价值。在黄河源头,卫星图像并不能带来身体的在场,文献资料也不能传达切己的感受,那些行走过程中个人与天地的交流与对话,甚至是冲突在身体留下的印记,都是纸本知识无法抵达的。从表面上看,行走获得的知识是一种私人知识,但是它因为具有身体性、私人性,同时也具备了与公共知识进行对话,甚至参与改造公共知识的能力。“这也可能是我愿意到这片广袤高旷地带亲历一番的原因。如果要得到一些公共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依靠卫星地图和各种文字材料,就可以安坐书斋,作一次溯源之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河源》赋予了此次探源之旅以真实的知识密度与独特的精神价值。
近年来,文学界、历史学界以及媒体界涌现一股“行走热”,至今依然连绵不绝,蔚为大观。如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李敬泽以“在大地上行走,看本真的黄河”为信念的《上河记》,以及阿来本人“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的《西高地行记》,这股文化风潮已重构了当今知识界的思想景观。尽管这些行走者关注的对象各异、书写的路径不同,但他们共同指向一个宏大而恒久的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更重要的是,在天地对话、天人之问中,在历史和现实的往返中,回应着我们当下的精神状况,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精神之问。
今天的人们身处加速社会,不可避免陷入双重失落之中。一是附近的失落,二是远方的遗忘。行走,正是在这两重失落之间展开的回应:回到附近,本质上是要从大他者回到个我,从陌生人世界拉回到熟人/半熟人社会,回到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世界;重走远方,则是在山河之间、山野之上融入自然、对话历史,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旷野写作,也是一种行动写作,更是一种面向历史、传统和天地的超越写作。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山河文明,《大河源》所倡导的今日之“远行”,则是现代人以回溯的方式逆入文明母体,以一种新鲜的眼光和视角重新打开山河以及背后的文明世界,进而在与当下对话中重新构建失落的意义世界。
总之,《大河源》躬行的远行虽然是个体的、私人的,但因为切中了时代的脉搏,而获得了公共性、普遍的文化乃至文明之意义。(叶祝弟)
